我的位置:页游 > 问答 《......也是亲情》
问《......也是亲情》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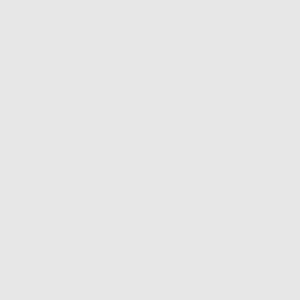 老虎不卖
老虎不卖
-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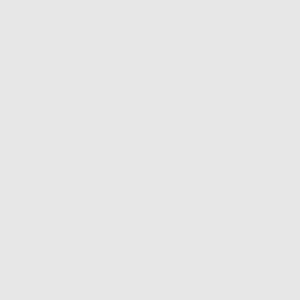 小仙女呀
小仙女呀
恐怖的利镞忽然穿透我的心了。在我生存时,曾经玩笑地设想:假使一个人的
死亡,只是运动神经的废灭,而知觉还在,那就比全死了更可怕。谁知道我的预想
竟的中了,我自己就在证实这预想。听到脚步声,走路的罢。一辆独轮车从我的头边推过,大约是重载的,轧轧地
叫得人心烦,还有些牙齿〖齿楚〗。很觉得满眼绯红,一定是太阳上来了。那么,
我的脸是朝东的。但那都没有什么关系。切切嚓嚓的人声,看热闹的。他们踹起黄
土来,飞进我的鼻孔,使我想打喷嚏了,但终于没有打,仅有想打的心。陆陆续续地又是脚步声,都到近旁就停下,还有更多的低语声:看的人多起来
了。我忽然很想听听他们的议论。但同时想,我生存时说的什么批评不值一笑的话
大概是违心之论罢:才死,就露了破绽了。然而还是听;然而毕竟得不到结论,
归纳起来不过是这样—
“死了…”
“嗡。这…”
“哼!“啧。唉!我十分高兴,因为始终没有听到一个熟识的声音。否则,或者害得他们伤心;或则要使他们快意;或则要使他们添些饭后闲谈的材料,多破费宝贵的工夫;这都
会使我很抱歉。现在谁也看不见,就是谁也不受影响。好了,总算对得起人了!但是,大约是一个马蚁,在我的脊梁上爬着,痒痒的。我一点也不能动,已经
没有除去他的能力了;倘在平时,只将身子一扭,就能使他退避。而且,大腿上又
爬着一个哩!你们是做什么的?虫豸!事情可更坏了:嗡的一声,就有一个青蝇停在我的颧骨上,走了几步,又一飞
开口便舐我的鼻尖。我懊恼地想:足下,我不是什么伟人,你无须到我身上来寻
做论的材料…。但是不能说出来。他却从鼻尖跑下,又用冷舌头来舐我的嘴唇了
不知道可是表示亲爱。还有几个则聚在眉毛上,跨一步,我的毛根就一摇。实在
使我烦厌得不堪,—不堪之至。忽然,一阵风,一片东西从上面盖下来,他们就一同飞开了,临走时还说—
“惜哉!我愤怒得几乎昏厥过去。木材摔在地上的钝重的声音同着地面的震动,使我忽然清醒,前额上感着芦席
的条纹。但那芦席就被掀去了,又立刻感到了日光的灼热。还听得有人说—
“怎么要死在这里?这声音离我很近,他正弯着腰罢。但人应该死在那里呢?我先前以为人在地上
虽没有任意生存的权利,却总有任意死掉的权利的。现在才知道并不然,也很难适
合人们的公意。可惜我久没了纸笔;即有也不能写,而且即使写了也没有地方发表
了。只好就这样抛开。有人来抬我,也不知道是谁。听到刀鞘声,还有巡警在这里罢,在我所不应该
“死在这里”的这里。我被翻了几个转身,便觉得向上一举,又往下一沉;又听得
盖了盖,钉着钉。但是,奇怪,只钉了两个。难道这里的棺材钉,是钉两个的么?我想:这回是六面碰壁,外加钉子。真是完全失败,呜呼哀哉了!“气闷!我又想。然而我其实却比先前已经宁静得多,虽然知不清埋了没有。在手背上触到草席
的条纹,觉得这尸衾倒也不恶。只不知道是谁给我化钱的,可惜!但是,可恶,收
敛的小子们!我背后的小衫的一角皱起来了,他们并不给我拉平,现在抵得我很难
受。你们以为死人无知,做事就这样地草率?哈哈!我的身体似乎比活的时候要重得多,所以压着衣皱便格外的不舒服。但我想,
不久就可以习惯的;或者就要腐烂,不至于再有什么**烦。此刻还不如静静地静
着想。“您好?您死了么?是一个颇为耳熟的声音。睁眼看时,却是勃古斋旧书铺的跑外的小伙计。不见
约有二十多年了,倒还是一副老样子。我又看看六面的壁,委实太毛糙,简直毫没
有加过一点修刮,锯绒还是毛毵毵的。“那不碍事,那不要紧。他说,一面打开暗蓝色布的包裹来。“这是明板
公羊传》,嘉靖黑口本,给您送来了。您留下他罢。这是…”
“你!我诧异地看定他的眼睛,说,“你莫非真正胡涂了?你看我这模样,
还要看什么明板?“那可以看,那不碍事。我即刻闭上眼睛,因为对他很烦厌。停了一会,没有声息,他大约走了。但是
似乎一个马蚁又在脖子上爬起来,终于爬到脸上,只绕着眼眶转圈子。万不料人的思想,是死掉之后也会变化的。忽而,有一种力将我的心的平安冲
破;同时,许多梦也都做在眼前了。几个朋友祝我安乐,几个仇敌祝我灭亡。我却
总是既不安乐,也不灭亡地不上不下地生活下来,都不能副任何一面的期望。现在
又影一般死掉了,连仇敌也不使知道,不肯赠给他们一点惠而不费的欢欣。我觉得在快意中要哭出来。这大概是我死后第一次的哭。然而终于也没有眼泪流下;只看见眼前仿佛有火花一样,我于是坐了起来。一九二五年七月十二日。这样的战士
鲁迅•
要有这样的一种战士—
已不是蒙昧如非洲土人而背着雪亮的毛瑟枪的;也并不疲惫如**绿营兵而却
佩着盒子炮。他毫无乞灵于牛皮和废铁的甲胄;他只有自己,但拿着蛮人所用的,
脱手一掷的投枪。他走进无物之阵,所遇见的都对他一式点头。他知道这点头就是敌人的武器,
是**不见血的武器,许多战士都在此灭亡,正如炮弹一般,使猛士无所用其力。那些头上有各种旗帜,绣出各样好名称:慈善家,学者,文士,长者,青年,
雅人,君子…。头下有各样外套,绣出各式好花样:学问,道德,国粹,**,
逻辑,公义,东方文明…
但他举起了投枪。他们都同声立了誓来讲说,他们的心都在胸膛的中央,和别的偏心的人类两样
他们都在胸前放着护心镜,就为自己也深信在胸膛中央的事作证。但他举起了投枪。他微笑,偏侧一掷,却正中了他们的心窝。一切都颓然倒地;然而只有一件外套,其中无物。无物之物已经脱走,得
了胜利,因为他这时成了戕害慈善家等类的罪人。但他举起了投枪。他在无物之阵中大踏步走,再见一式的点头,各种的旗帜,各样的外套…
但他举起了投枪。他终于在无物之阵中老衰,寿终。他终于不是战士,但无物之物则是胜者。在这样的境地里,谁也不闻战叫:太平。太平…。但他举起了投枪!
-
问 范冰冰魔法学院攻略粉色心情亲子提问时间:2024-07-27 23:16:09答 衣:紫色性感透视上衣 裙子:紫色柔纱长裙 鞋子:闪片运动鞋 发型:可爱小马尾 都是在衣帽间或者化妆间就能买到的,都是用钱的,不需要用钻石。这样就能有五星了
-
问 有谁能够救救我即将被亲情湮灭的爱情?提问时间:2024-07-27 20:26:26答 姐妹,别太傻了,这个世界的爱情很不廉价,我哥哥也是个当官的,虽然是个村官,我父母也是不会同意自己的儿媳是没有“工作”的人,更何况你的父母还是当官的,更不会让这样...
-
问 亲人动手术时你在外等候,这是怎样的一种心情?提问时间:2024-07-27 20:47:56答 其实这个和患者有关,如果知道这是一个很简单的手术,也不会出现意外,时间久点也无大碍。如果是有一定风险的手术。在外等待肯定会很焦虑。
-
问 求bl**文~~,不是bl也行,照单全收,打包传上来吧,亲们~~提问时间:2024-07-27 20:58:54答 展开全部《身份系列之**》作者:梨花烟雨/梨花院落《**鬼娃娃》作者:沉默天渊《血蝴蝶》作者:忘情(强攻强受,**,**)_《风住尘香》作者:上官飞雪(痴**手...
-
问 梦幻恋舞情侣亲密值怎么增加 情侣亲密值快速增加攻略提问时间:2024-07-27 09:47:19答 使用相思红豆 可通过完成任务、幸运阁抽奖、完成一曲舞蹈后随机抽奖获得使用蜜汁糖果 可通过完成任务、在商城购买、幸运阁抽奖获得使用浓情巧克力 可通过完成任务、在商...
-
问 情侣空间如何增加亲密度?提问时间:2024-07-27 00:34:24答 如果双方都不是黄钻那每天只能加10分 如果有黄钻(不管是你还是他)就按等级加分 比如 你现在是5级,你对象是3级 那每天就是15分(按等级高的一方)我现在是4级...
-
问 你觉得钱真的比亲情还重要吗?亲人之间怎么处理好金钱关系?提问时间:2024-07-27 16:38:47答 亲情是让人感觉很踏实很安全的一种关系,但一旦掺杂了钱,很多亲情变的单薄,甚至剑拔**张、反目成仇。如何处理亲情和金钱的关系,我觉得有句古话很有道理,所谓“升米恩...
-
问 关于亲情的美段提问时间:2024-07-27 19:52:47答 1.在最无助的人生路上,亲情是最持久的动力,给予我们无私的帮助和依靠;在最寂寞的情感路上,亲情是最真诚的陪伴,让我们感受到无比的温馨和安慰;在最无奈的十字路口,...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